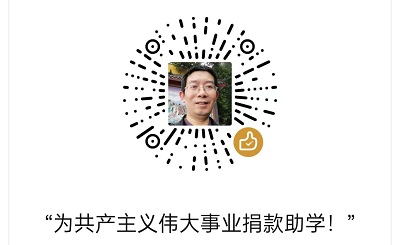时间:2025-02-23 15:31点击:26
原创 智者说哲理箴言 智者说工作室 2025年02月22日
为什么寄希望于民哲?
智者说
一位朋友把我拉进一个哲学微信群。从发言可以看出,群内可能有几个专业学者,一讲到“这段话的英文翻译是这样的……”类似的话,令我不由得心生敬佩。我也曾在群里发过言。然而,令我惆怅的是,当我道出一个观点时,群内总是会出现一时间的沉默。而当我对某个学者的发言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,自然也招来了批评的声音。
有人批评我说,我在阐述哲学观点时,语言过于文学化,不是规范性的学术语言。言外之意,他们一接触这样的语言,就感觉到味道不对,我如此使用语言不是正规地研究哲学。这种论调,在网络学术讨论时,也有的网友提出过。我对他们说:语言的本质目的是什么?如果我所使用的语言较那些晦涩的学术语言更容易被人所理解,并有什么不好。
群里还有人批评我“不读书”,自己在那里瞎想,而想出来的东西,其实别人已经说过了。我要说的是:非常感谢,我最担心的就是怕别人说我不动脑子想。一个想要研究点什么的人如果不知道开动脑筋去想,那是顶糟糕的事情了。即便是我想的东西别人已经想过了,那也没关系——第一,同样的道理,我自己想的,必是活在我心里,而不是别人硬塞进我心里的;第二,我想到的总归会有我的思考痕迹,总会和外在的东西有所差别;第三,我继续思考下去,总会有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思考结果。相反,如果你不懂得自己去想,永远也不会有属于你自己的思想。有人说,我们就是要抱着一种学习的谦恭。我以为,貌似坚守着一种美德,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矮化。你和那所崇拜的大师一样,同样有着思考的机能,为什么你天生就该放弃?有人张嘴胡塞尔,闭嘴海德格尔,和政治一沾上便,便扯到哈耶克怎么说的了。这种讨厌的文风,和文革时期讲用文章、心得体会文章本质是一样的,只是把马恩列斯毛换做了他们眼中的近现代西方“大师”。
我不是不读书。除了写自己的东西,我就是看别人的东西。我出版的《智者说》一书,就是从数百万、甚至上千万字的笔记卡片中选择编撰的。但是我反对死读书,被书牵着鼻子走。我所强调的是:“我读书,我是主体”。如果书中的一段话,或者一个词引发我的思考,我便自己想开去了。我写东西,很少引用别人的话,没有什么人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,没有什么人的观点可以作为论据存在。
反思钱学森之问,我们的大学教育之所以“出不了大师”,问题的关键,就是我们的教学一直循着引导学生读死书的路子走。讲这个大师,讲那个大师,满脑袋都是这个是怎么说的,哪个是怎么说的,就是没有学生自己的“我认为”,以至于我们在讨论问题中面对的,就是这样一群“会说话的U盘”。
严格地说,我虽然也上过大学,可毕业以来一直从事实际工作。就哲学研究而言,终归还属于民间的野路子。于是便想到了院哲与民哲的问题。
到底有没有院哲与民哲之分呢?记得在2012年3月,由中国学术论坛举办、有陈嘉映、赵汀阳等专家学者参加的民间哲学对话会上,陈嘉映老师谈到,他也曾经是一个民哲。下乡时经常和哥哥,还有几个同好讨论哲学问题。如今,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大学里的哲学教授了。在我想来,院哲与民哲的区别还是存在着的。
院哲努力坚持着一种所谓的学术纯正,但是脱离实践,脱离生活,脱离大众。他们所乘坐的,是一代代的老师提供的轨道交通工具。坐着很舒服,目标也明确,那就是到达那个城市,进入那个庙堂。他们一路上所能看到的,都是有限并一致的风景,如果有人再低着头不看窗外,则是该看到的风景也没有看到。他们最终变成了“一个行走着的u盘”。他们已经可以放弃那种绞尽脑汁,劳神费力的写作了,因为ai比他们写的更好。
民哲则不同,他们的交通工具五花八门,有些人甚至是光着脚走路,关键是他们没有规定的线路。这种旅行,对于一些民哲来说,很难走的很远,也绝少有人能够获得世俗的利益;对于一些民哲来说,他们看到的也许仍然是人家乘坐着轨道交通工具所看到的东西;对于一些民哲来说,看到一处风景便欣喜若狂,流连忘返,“障”在那里了;然而,正因为民哲脱离了规定的轨道,可以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地四处寻觅,才会有新奇的发现。由此我坚信,未来哲学的发展,一定有赖于民哲。
我曾经把一个同样的题目分别交给deepseek和miki去写,结果分别得到了两个不同的文案。观点大体差不多,但语言有区别,内容有长短。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观点的新颖度不过如此,都是从现有的数据库中来的;第二,既然有区别,就说明没有哪个智能模型是最终的顶配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,如果你只会背书,你存在的意义甚至不及ai,而民哲那种五花八门、奇思异想的创造性的思维则显得尤为必要。